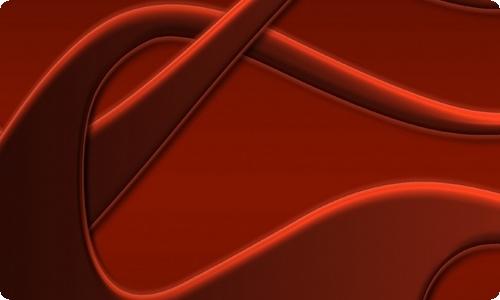记忆中的那双手作文

记忆中的那双手作文
在日常的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中,大家一定都接触过作文吧,写作文可以锻炼我们的独处习惯,让自己的心静下来,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。那么一般作文是怎么写的呢?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记忆中的那双手作文,欢迎大家分享。
记忆中的那双手作文1
“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……”满天星斗眨巴着眼睛,耳边传来昆虫的浅吟低唱,温暖的手掌轻轻拍打着我的背。外婆手里摇着的蒲扇带来丝丝的凉意。仔细看了看那摇蒲扇的手,圆润、结实,红彤彤的手掌里不知不觉滋生出几条细长的纹路来。
童年的时光犹如滑过指尖的细沙。换上了小学的校服,去往学校大门的路上,路旁的花草随风摇曳,像在和我道着早安。和煦的春光洒在每一条大道上,似乎给这宁静的画面加上了一层滤镜,过滤出了霓虹般的色彩。牵住我的那双手传来的温度温暖着我的心房。蹦蹦跳跳地来到红绿灯前,刚要踏出脚步的那一刻,牵着我的那双手猛地一紧,将我硬生生地拽了回来。飞驰的车辆从眼前呼啸而过,留下浓厚的黑色的'瘴气。我不由地重咳几声,那双手又轻轻抚着我的背,使我安心下来。无意间,又看了一眼那双手,手背上出现了许多白色的零星状的斑点,或许是长时间将手浸泡在肥皂水里,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养才会出现的,心里不由地一怔。指尖轻轻划过湿润的手掌心,明显感觉到没有以前那样的光滑圆润,手上的纹路愈深愈粗,犹如山涧的沟壑一般。
钟总是越拨越快的。悄然间,时间已经拨到了初三。闲暇时不甘拘泥于书本,便跑到厨房探出脑袋。外婆坐在一张小木凳上,正择着黄芽菜。阳光缠绕在外婆本就稀疏的银丝上,她那布满血丝的眼睛专注地盯着黄芽菜,弓着背。先用手将塑料袋里躺着的黄芽菜拨散开来,拣起一撮,便开始择菜了。她的指甲如锋利的刀片,将黄芽菜底部几根灰色的长须切割下来。当我再一眨眼时,手上又是一撮新的黄芽菜。抬起头看到我时,便招呼我过来。我搬了一张木凳与外婆相对而坐,接过一把黄芽菜便折了起来。刚刚才折下一根黄芽菜的我便开始嫌弃折菜时溅出的菜汁,皱了皱眉头,撅起嘴唇“啧”了一声。外婆早已看透我的心思,伸手便来接我手里的那把黄芽菜。恍惚间,我又看清了那双手:泛白的指甲染上了淡黄色的菜汁,杂乱的白色条纹在手背上交织出一个又一个“井”字,手心如小溪干涸后留下的一块平地,突起的腕骨让人触目惊心,眼眶变得湿润起来。再近一些,手上突起的青筋激起我心中阵阵涟漪。触碰到了那双手时,那从未感受过的粗糙感让我不由地把手一缩,但我随即又紧紧地握住了那双手。糙如枯树的手背宽大而又温暖,如阳光投射在枯老的树干上一般。
岁月无情地将那深深的沟壑刻在了那双手上,那双曾经带来的凉爽的手,那双传递给我温暖的手,那双给家人带来美味佳肴的手……眼泪不住地在眼眶中打转。我想,外婆一定是摘下了天上的繁星,将它嵌在了自己的手背上。
每当我看到这双手,总能想起那个朦胧的夏夜,那朦胧的呓语,只不过,多了一份夺眶而出的眼泪。
记忆中的那双手,如果可以,我想主动牵着这双手,好好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。
记忆中的那双手作文2
每次来到太爷爷坟前,我总是“读罢泪沾襟”。碑上的太爷爷像总能让我想起那双手。
我开始懂事时,太爷爷已是一位年至耄耋、苍颜白发的老人。他的手皮肤粗糙得跟树皮似的,松弛且布满老年斑。五根手指头瘦得像五根树枝,手上的青筋都突露出来。
然而,年迈的太爷爷依然乐天知命,他的那双手也十分灵巧,能把大大小小的木块变成小人、空竹、佩刀等工艺品。有一次,我亲眼看到他手握着他的老佩刀,活生生地把一块小木头变成一只小舟,以至于后来学《核舟记》时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太爷爷和他那双灵巧的手。
太爷爷最擅长的是做陀螺。
太爷爷做陀螺,我就爱在一旁看。太爷爷左手握着一块圆木,右手攥着他的老刻刀,眉头紧皱,一刀一刀小心砍着、削着。他额头上的皱纹紧紧地密集在一起,他的手犹如黄忠出阵——不服老,小心且灵活地游走着。随着他手起刀落,一片片小木片和木屑飞起又落下,圆木的一端渐渐被削尖。过了没一会儿,一只精致的陀螺完工了。
太爷爷对我说:“牛牛,我来教你抽陀螺吧。”说着,他把陀螺立在地上,然后用他的老手紧握鞭子对准陀螺猛地一抽,陀螺飞速旋起来,我也学着太爷爷的做法让陀螺继续旋着。
陀螺不停地旋着,我渐渐长大了,太爷爷开始用他的大手把持着我的小手教我做陀螺。我的小手模仿着大手的动作,居然也学会了。
可天有不测风云,不久后太爷爷被查出肺癌晚期住了院。
第二天,我去探望太爷爷时发现他手里又攥着圆木和刻刀,便问:“太爷爷,您还做陀螺呢?”太爷爷笑着说:“好久不做了,手痒了!”太爷爷的手已不复当年之勇,两只握着圆木和刻刀的手都在不住地抖动着,每下一刀都要吃力许多。
约莫五天后,我发现太爷爷已到弥留之际,不久便去了。那双致力于手工工艺几十年的手停止了工作。我趴在窗台上,凭轩涕泗流。
去年清明,我和几个堂兄弟去太爷爷坟前扫墓,回家后对他们说:“我们做几个陀螺吧。”可他们态度冷淡,说:“你还玩这个?早过时了!”
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,取出一块圆木,又请出那把老刻刀,我要自己再做一个陀螺给太爷爷看。
我静下来,沉入太爷爷做陀螺时的那种心境:仔细、专注,将一切置之度外。顿时,周围万籁俱寂。
我攥紧刻刀,双手努力地重复着太爷爷的手的运动轨迹,缓慢地在圆木上刻下一刀又一刀。圆木的一端慢慢变尖了,陀螺慢慢地成型了。我仿佛感到太爷爷冰凉的手从远处伸来,接通了我手上的温度;我仿佛又听到太爷爷爽朗的笑声从远处传来,在我的耳边响起。我并未抬头,依然埋头对着圆木砍啊、削啊,眼睛竟莫名的湿润了。
透过模糊的泪眼,我惊奇地发现,那双属于青年的略呈棕色的手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那双粗糙、布满皱纹的老手,紧握着那把有点生锈的老刻刀,对着圆木砍啊、削啊……

文档为doc格式